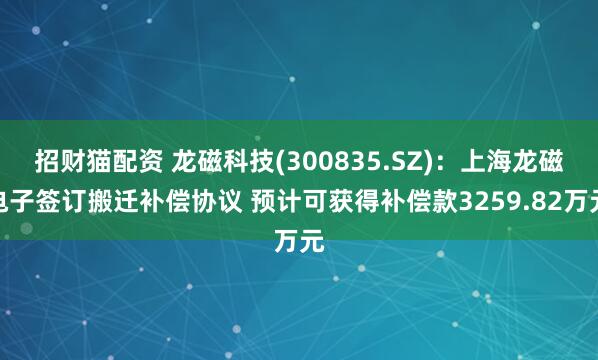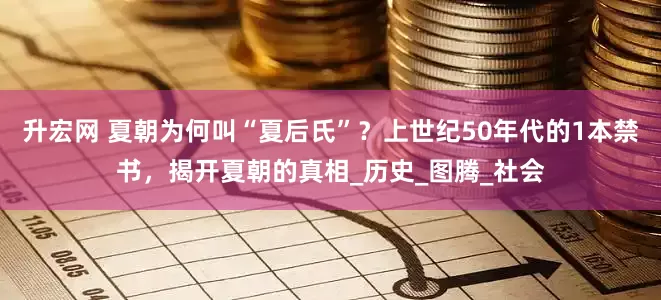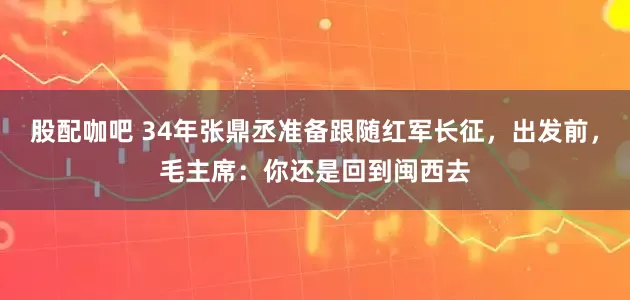
“1934年10月18日夜股配咖吧,你明天就跟着部队出发?”窑洞里,灯芯噼啪作响,毛泽东的语气平静而坚定。张鼎丞点头,他的行囊已经打好。可毛泽东接下来的话,让他怔住:“闽西更需要你,你熟门熟路,留下去,坚持游击。”短短一句,把决定权又推回到张鼎丞面前。

外边是连绵秋雨,窑洞里一时安静得只能听见水滴声。张鼎丞脑子迅速转了一圈——长征是中央红军的生死大计,跟着走,安全系数也许更高;留在闽西,等于扎进敌人的围堵网。但他明白,闽西是自己的根,他更清楚毛泽东深思熟虑后才会开这口。片刻,他抬头,只回了两个字:“遵命。”
决定落地,必须有人马上去通知后勤,把他备好的马匹、枪支、干粮转给其他同志。张鼎丞握住毛泽东伸来的手,掌心粗糙,却传来一股暖流。毛泽东没再说客套话,只补了一句:“缺什么就写信,苏区无,但我想办法。”
张鼎丞1898年生在福建永定,贫苦出身,读过私塾,在村小当过启蒙先生。1927年“白色恐怖”最浓时,他瞒着家里人,跑去汀州秘密宣誓入党。周围很多师生劝他“躲年风头”,他一句话顶回去:“拼命读书就是要救人,怎么能一转身只顾自己?”

1928年6月,他组织溪南区数千农友拿着长矛火把攻下永定县城,救出被捕同志。县衙大门在火光里轰然倒塌,城内富绅吓得连夜外逃。有意思的是,这场暴动只坚持了三天,却像一把铁钳,死死夹住了敌人对闽西的注意力,也为随后红四军进入福建铺了路。
毛泽东率红四军挺进闽西那年股配咖吧,第一次与张鼎丞长谈。两人谈的不是“官职”,而是如何在土壤贫瘠、宗族盘根错节的闽西发动群众。讨论结果极其朴素:一靠土地政策,二靠本地骨干。于是张鼎丞被推上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位置,打仗、分田、办学样样沾边。

1933年“左”倾路线盛行,罗明坚持打游击、避硬拼,张鼎丞公开支持,结果双双成了“靶子”。他被撤职,调到中央政府粮食部挂名副部长,实则挑着扁担在乡间收粮。很多人替他鸣不平,他却私下一笑:“干革命,不能只盯着帽子。”不得不说,这种心态,让他更得民心。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已成定局。中央决定突围西去时,张鼎丞本来被编入纵队随行,连行军口令都背熟了。毛泽东另起一笔的人事安排,让他掉头回闽西,“就地坚持”的责任大过天,大后方一下子成了前线。

闽西山高林密,土匪、地方武装、国民党封锁线层层交错。游击队常常白天猫在山洞,夜里急行几十里。有人回忆:“他那时咳得厉害,走十步就喘。”可只要敌人逼近,他仍扛枪冲在前头。最艰苦那阵子,连树皮都快剥光了,张鼎丞索性把自己那点炒米省下来给伤员。战士劝他:“司令,你也得吃啊!”他笑着举起空碗,“我胃口小,省点伙食。”
1936年冬,金丰大山缺粮,队伍派人轮流下山背稻米。张鼎丞因久病被留守,他却挑起另一件“大事”:烧水、煮饭。一锅糙米饭香气四溢,士兵一进门先愣住,随后大口扒饭,脚泡在热水里,连夜色都显得不那么冷。有人小声嘀咕:“闽西真把咱们司令给饿成炊事班长了。”

卢沟桥枪声响起后,南方各路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。张鼎丞被任命为第二支队司令员。他带队北上皖南,第一件事就是选址办训练班,整顿队伍。新兵操课时他常在一旁看,遇见姿势不对就冲过去亲自示范,胳膊上旧伤疼得发抖还咬牙硬撑。一个安徽籍新兵说:“福建口音听不全,但他动作大家都看懂了。”
1939年,党中央电令张鼎丞赴延安。五年南方山林岁月,他瘦得脱相,穿军装显得空荡。毛泽东在窑洞门口等他,握手时调侃:“路遥知马力,老张还行吧?”张鼎丞鼻头一酸,粗声答:“马力一般,蹄子还在。”一席谈后,毛泽东评价南方坚持游击“等于第二次长征”。这份肯定,对闽西游击队来说,比任何奖章都珍贵。
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,张鼎丞调往华东支援粟裕部队,随后又重返福建主持省工委。建国后,他接连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、华东行委副主席、中央组织部副部长,1954年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,成了共和国法制战线的“守门员”。他的简历页页风光,背后却是闽西山林里的硝烟味。

临终前,他对闽西老战友只说一句:“没把山里人饿着,算我一点心安。”话不长,却把他一生的轻与重、得与失交代得明明白白。当年那句“你还是回到闽西去”,像一把钥匙,将他的命运牢牢扣在那片红土地上,也把闽西游击火种保存了下来,最终与全国胜利的星火汇成燎原之势。
顺阳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